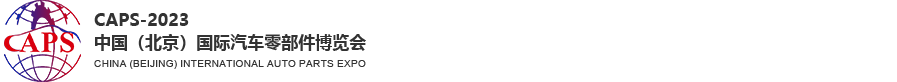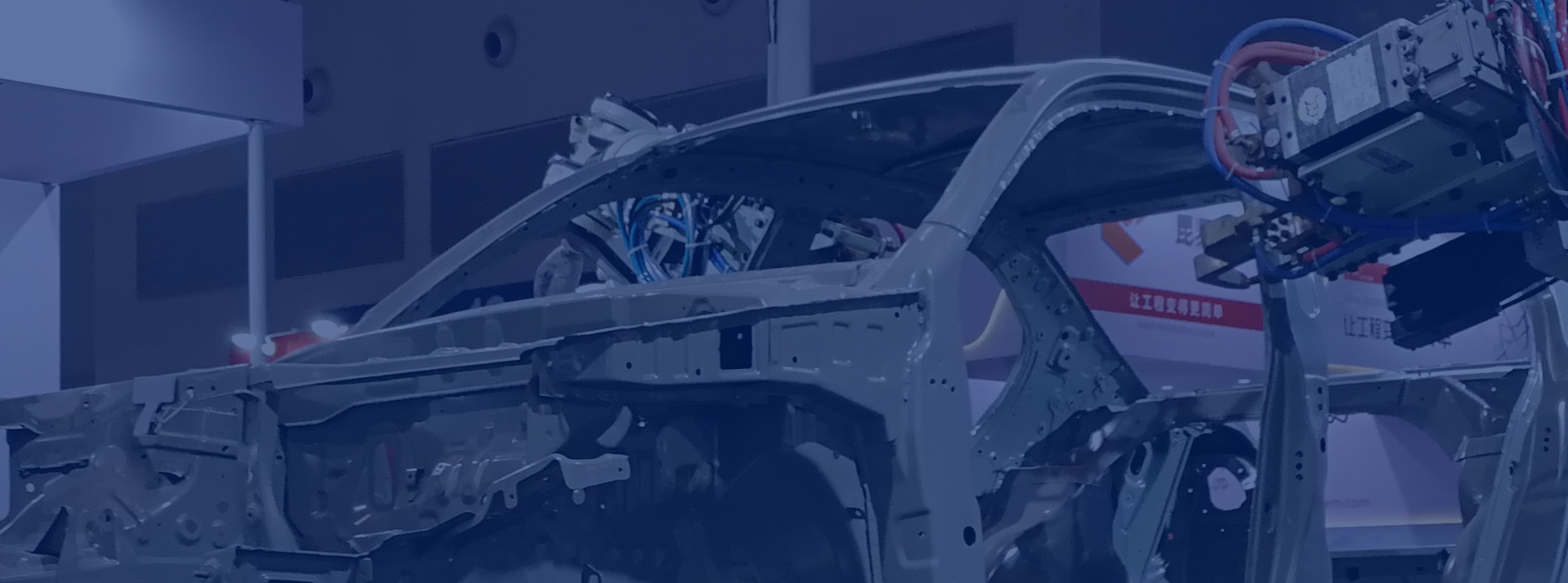由俄烏沖突、美聯儲加息以及中國防疫疊加的不確定因素,導致全球經濟衰退的可能性愈發突出。
摩根士丹利在最新的研報中預警:我們生活在幾十年來最混亂、最難以預測的宏觀經濟時代,誘發全球經濟衰退的眾多因素已“浮出水面”。
實際上,即使不用看經濟數據,多種信號已持續傳出:殼牌中國裁員、佳能珠海撤離、三星天津撤離,為數不少的跨國企業出現新的動向。具體到汽車業,短期考慮復工復產,中長期則要考慮產業鏈外遷的風險。
當勞動力成本優勢不再,當地緣政治紛爭逼迫制造業回流,當疫情影響整個社會經濟活動,中國還能留得住汽車產業鏈嗎?
沒有政策工具能讓制造業回流美國
制造業產業鏈外遷,從來不是新話題。從2012年美國提出重返亞太戰略,到特朗普上臺后中美貿易摩擦升級,再到近兩年來疫情攪亂了世界,特別是3月份上海封城以來,整個產業界更加緊張。
美國在華商會表示擔憂,稱82%的在華美國制造商生產受到影響,57%企業認為疫情(管控)阻礙了供應鏈,86%企業表示供應鏈中斷,54%企業削減了今年營收預測,29%的美國企業表示推遲在中國投資,17%的企業則已經減少投資。

但從商務部1月份數據來看,2021年全國實際利用外資1.15萬億元人民幣,同比增長14.9%,規模再創新高。
今年疫情此起彼伏,投資規模預計不會超過去年。美國已經加息了兩次,75個基點,預計每月都會加息,聯儲威脅稱要一路加到3%(基準利率)。
美國有經濟學家表示,就算加到5%,史詩級通脹也未必壓得下去,但美股好像已經快崩了。美國一加息,各國(特別是新興工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)外資將回流美國。這是可以預期的,但沒辦法抗衡,就是如何承受的問題。
但是,美國加息不可能太高(3%都不大可能),否則利息就付不起了。美股崩了,還不是致命傷;美債爆了,絕對是王炸。
壓通脹的最好辦法,就是和中國進行貿易緩和。耶侖和戴琪時不時釋放點降關稅的口風,就是不見動靜,可見內部并未取得一致。中國這邊依舊不接招,反正通脹不是痛在自己身上。

特朗普政府的制造業回流政策,貌似治本,實際上治了個寂寞。美國現在就連在毛利率達到40%的芯片行業都無法獲利(即便拋開專利所有權的問題),指望美國重新成為一個全產業鏈國家,似乎是奢望。
今年3月,鮑威爾也表示,利率工具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鑰匙。但2020年鮑威爾聲稱,致力于使用所有工具,確保經濟強勁復蘇。其實,且不說利率就是美聯儲工具箱里唯一的工具,認為其能解決產業問題,恐怕就有點強人所難了。
那么問題很清楚了,在華汽車零部件企業,不管是歐洲的,還是美資的,都不會考慮回到美國。
產能部署規律很簡單
跨國汽車零部件生產商的產能部署考慮很簡單:距離客戶更近、距離終端市場更近,最起碼距離交通樞紐(港口、空港等)更近,然后才是勞動力、土地、稅收、金融等因素。前三個要素是物流,后四個和財務直接相關。而以上所有因素,都可以歸結為成本要素,包括時間和機會成本。
還有一點,汽車是長鏈、強周期行業。如果產能部署變更(也就是搬遷),如果不是站在跨周期的時間高度考慮,那么就可以被無視,基本上就是抱怨幾次,回頭該干嘛還干嘛。就像兩個商會日常做得那樣,如果以為他們對國家政策有影響力,純屬想多了。

本來,零部件企業沒有那么上頭,管你什么政治體系。但今年不同于往日,地緣政治風險全面爆發。不考慮政治因素,不是合格的跨國企業。
不用管商務部的“形勢大好”的數據(相當滯后),中國未來隨著收入提高,建廠成本也在不斷提高,沒有辦法、也沒必要保有全產業鏈要素。天要下雨,娘要嫁人,隨他去吧。要服從經濟規律,不要干美國上屆政府那種傻事,完全沒希望。
低端制造早晚保不住
哪些要走?零配件里面低技術含量、高污染、勞動密集和附加利潤低的那一部分。有些小朋友問,為什么不往內地轉,東西部差異還可以吃一波……其實即便是不考慮產能調配因素(西部生產的零部件供應海外的話,多出來的物流成本誰來付),也沒啥戲。
很多人對中西部四五線城市生態不大了解。這種地方有兩種業態:一種是往附近大城市輸送服務的;另一種是本地服務。
前者包括OEM輻射出來的上游環節,后者則是一堆必須本地配置的內容,什么家政、安裝、配送、水電暖等服務。即便是后者,低工資(譬如2000元/月),也能招到人,但都是老婆婆、老大爺在做。只要你看到小區保安的平均年齡蹭蹭地漲,就知道中國勞動力已經不那么富裕了。

但是富起來也有好處,就是市場在這,誰也搬不走。零部件企業就算在國內開廠不合算,想跑路,也只能圍著中國打轉轉,不至于跑到墨西哥去,那是給美國做配套才會潤的地方。
還能是哪兒,只能是東南亞,再加上印度洋三兄弟(印巴孟)。后者因為離中國的距離,比東盟吃虧。這里面越南的聲勢甚囂塵上,輿論各種吹捧就不一一復述了。
“越吹”的邏輯硬傷
但是要清楚,越南因為體量、地理位置和國家精神內核的關系,不是更早階段的中國,而是跟在中國后面撿點殘羹剩飯的小弟。靠著給中國做配套,或者當中國的馬甲而存活。
前者大家都能理解,后者則源于中美貿易戰正酣的時候。“Made in China”運到越南標簽一撕,貼上“Made in Vietnam”然后出口美國,越南兄弟賺點中轉費。這是以前香港才有資格干的事,現在俏錢掙得樂不思蜀。

越南的鐵路設施早就陳舊了,主體還是法國人建的那一套。越南國會搞了2030年規劃提出,資本需求240萬億越南盾。重點是建一條縱觀全國的鐵路,1559公里長,設計時速350公里/小時(運營速度320公里/小時)。聽上去這個指標很中國,其實這份報告在2010年就已經提交國會,比中國高鐵大建還要早。被否了之后過了10多年又原樣端出來,就改了個年份。
越南官方做規劃的還是很有AC數,知道憑越南自己搞不定,聲稱:“政府需要聘請獨立的外國咨詢單位編制可行性報告,然后國際招標吸引更多外國企業參與”。
看到沒?就連甲方需求書,都沒能力寫,還提什么350公里時速。如果越南能在2045年前搞定這條線,就承認他是中國工業產業接班人。
越南未來10年的現實,就是踏踏實實“擰螺絲”和“貼標簽”。想走中國重工業+基礎設施+全民通識教育開路的做法,且不說錢的問題,越南的體量,每年能培養多少基礎設施合格工程師?
給中國做配套仍是未來的現實
現在中國的汽車業生產,正處于升級和長尾并存的“怪獸時刻”。前頭升級,已經和德日美品牌干起來了,尾巴則在和越南、大馬、印尼等搶食。后面那些是可以隨著時間推移棄掉的(不等于現在放棄),前面必須拿下。
中國汽車零部件從2003年(入世兩年后)崛起,10年內年均增長率達到25.7%,出口比重累計上升了14%,用10年走完了德日美50年的路。
就從那時(2003年)起,跨國零部件企業紛紛來中國投資建廠,一方面供應本土需求,另一方面是出口。全球汽車零部件貿易網絡的核心就從美國和日本,逐漸向中國、德國傾斜和轉移。特別是在電子電器組件、輪胎和內胎組件等領域,中國供應商具備相當的優勢。

現在中國明顯向電動產業鏈轉移,這一塊沒人有實力全面爭搶(韓國可以分食電池)。外國生產商對疫情處理方式(動態清零)有抱怨,無非是不讓開工、物流停滯,耽誤了賺錢。他們可能將一些低端制造能力分給周圍國家,但核心部分必須在中國。整個東盟面對中國的逆差,有相當一部分就是因為中國居于產業分工的上游。
越南必須等著中國IGBT(英飛凌在深圳產線)才能組裝“三電”。為什么不把IGBT放在越南一部分?這就等同于問,為啥阿迪、耐克跑到越南、孟加拉去了,但是塑料件、橡膠件仍然要靠中國供應一樣。
如今,汽車OEM正圍繞區域中心進行整合,供應網絡會隨之出現區域化特征。簡單說就三個輻射帶:墨西哥輻射美國,東歐和摩洛哥輻射西歐,中國和東南亞輻射亞洲。
印度不止一次地表示自己組裝生產特斯拉更便宜,為什么馬斯克還要在上海建第二工廠(也有說只是新增產能)。關于供應鏈完整性和成本,特斯拉顯然比印度官員更有數。

中國汽車零部件企業超過10萬家,實現1500種部品全覆蓋,中間虧本的停掉幾家,無足輕重。有哪個供應商因為疫情管控,跑到沒有上下游配套企業的地方去開荒的?這事必須得OEM商牽頭,才有希望。
到目前為止,沒有觀察到任何周圍國家的OEM大規模新建產能,包括萬年潛力股印度。所以,關于產業鏈轉移和工業空心化的問題,在可見的未來,對于中國來說是個偽命題。而產業升級,則是另一個話題。